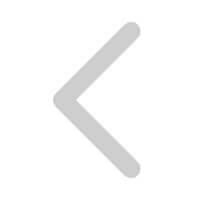 返回
返回
2019年和2020年澳大利亚前所未有的野火让人记忆犹新。而对于贝克心脏病与糖尿病研究所计算生物学家Michael Inouye来说,正是随着气候变暖更有可能发生的让其实验室关闭的野火,促使他开始关注碳排放问题,尤其是自己做研究时产生的碳排放。
2020年,Inouye与两名博士生合作,测量他们开展的计算研究产生的碳排放量。他们创建了一个可在线免费使用的“绿色算法”,用户可以通过该算法估计其研究项目的碳足迹,以达到减排目的。
比如去年,Inouye用该算法计算了其团队人类遗传学和饮食研究项目的排放量,并通过种植30棵树来“抵消”排放。
Inouye知道这种“抵消”做法是有争议的。对该做法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如果这些树没有得到适当的监管,就不能保证它们在能活着。“但我认为,做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Inouye说。
Inouye并不孤单。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天文学到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了解和解决其研究中的排放源,但真正做起来时并不顺畅。
比如,2019年,法国图卢兹天体物理与行星科学研究所(IRAP)的科学家测量了该机构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其中包括了用电、用水、取暖等所需的能源。
“研究发现,天文台是我们碳排放的最大贡献者。”IRAP天体物理学家Jürgen Kn?dlseder说,2019年,使用观测站数据造成的碳排放量为4100吨,相当于英国2050辆油气车全年运行所带来的碳排放量,因为运行天文台需要大量的电力。
这促使科学家们思考,当主要排放源是他们赖以突破的技术时,如何使相关工作脱碳。
Kn?dlseder说,一种选择是暂停收集新信息,转而对已存档数据进行研究。他已经和博士生一起开始了这样的项目。
生物医学研究也存在类似问题。英国爱丁堡大学神经学家Rustam Al-Shahi Salman表示:“临床试验,尤其是以特定方式设计的临床试验,可能会产生大量碳排放。”2021,他开展研究,提出了一项测量临床试验碳足迹的策略,相关工具正在测试中,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发表。
Al-Shahi Salman说,之前的研究就发现,两项测试皮质类固醇对脑损伤患者影响的临床试验的碳排放量在181.3吨至108.2吨之间。试验材料的运输和试验供电产生了最大的碳排放。
对此,Al-Shahi Salman表示,减少排放的一种方法是继续使用疫情期间的远程医疗策略,例如线上举行会议、获得患者同意后通过视频进行随访,或者让患者佩戴远程健康监测设备。
IRAP天体物理学家Pierrick Martin表示,大规模减少研究碳排放需要相关机构支持。“在个人水平上做的一些事情是有价值的,但是有限度的,在某个时候无法逃避相关政治决策的调控。”
Martin补充道,各机构现在应该做的是研究如何减少碳排放,而不仅是测量碳排放量。
 0
0 0
0
低沉旳呢喃
新时代必将是大有可为的时代








 下载文档
下载文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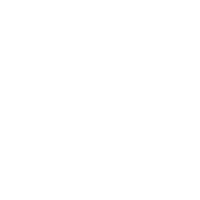
 微信支付
微信支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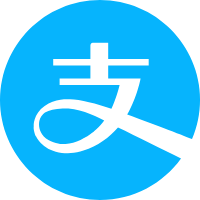 支付宝支付
支付宝支付